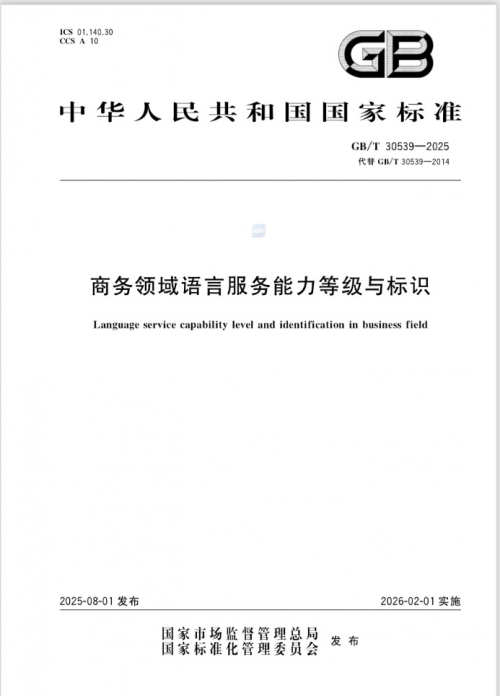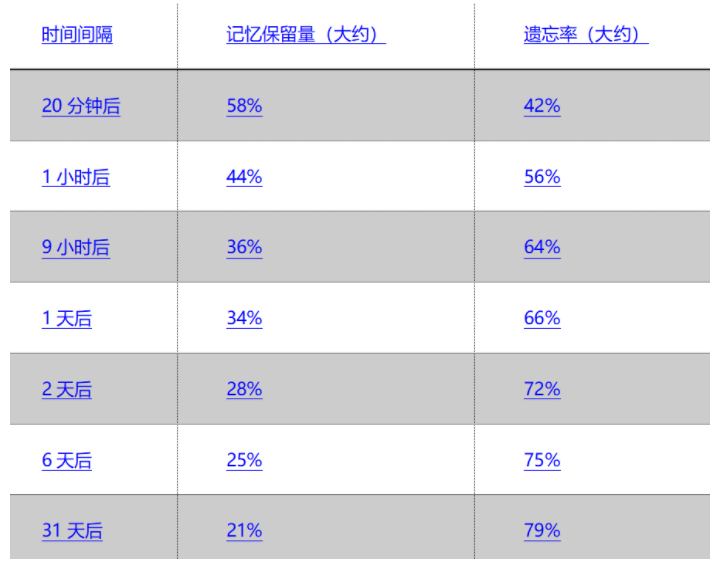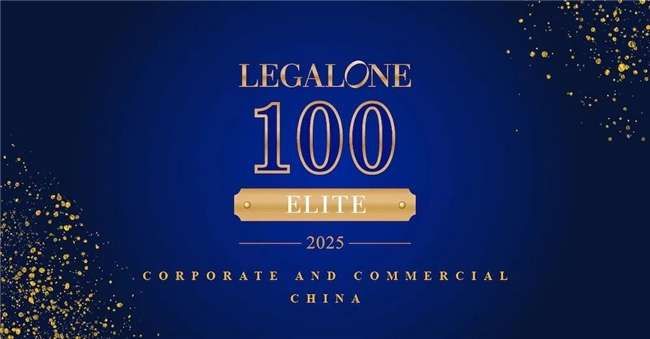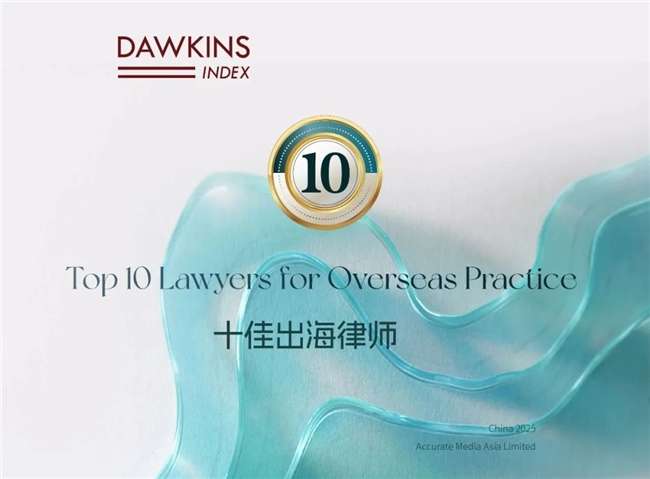导语
在纪录片导演詹佳骏的镜头里,“人生”不只是抽象的命题,而是一次次具体的经历——第一份工作的紧张、第二次机会的挣扎、在法律与社会夹缝中争取发声的坚持。通过《人生第一次·上班》和《人生第二次·是》,他不仅记录个人故事,更试图让被忽视的群体在影像中得到回应。在纪录片领域,他的作品曾获得许多重要奖项和提名,这些荣誉证明了他在叙事和影像表达上的独特价值。但詹导本人更愿意让作品自己说话。对他而言,纪录片的核心,是如何在被遗忘的人与事中,找到人性最质朴的光亮。
从“上班”看社会的温度
在《人生第一次·上班》中,镜头对准的是一群特殊的劳动者:因疾病或残障难以外出,却在云客服岗位上努力工作的年轻人。
“他们的故事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他们和别人一样渴望被当作普通人看待。”詹佳骏说。
影片展示的不只是个体的努力,还有社会的温度——无障碍设施是否完善?招聘机会是否公平?“当我们把镜头对准他们,其实就是在问社会一个问题:我们愿意用什么眼光看他们?”
“是”:制度与人的拉锯
在《人生第二次·是》中,詹佳骏把镜头带进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厅。观众看到的不是激烈冲突,而是检察官和申诉人长时间的对话、反复的案卷核查,以及法律逻辑与个人情感的艰难交锋。
“有人问我,这样的场景是不是太‘枯燥’,没有戏剧性。我不这样认为。”詹佳骏说。“纪录片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制度如何运作,以及人在制度中如何坚持。”
在他看来,“是”不仅是一个法律判断的词汇,也是社会在反复审视后作出的艰难回应。“法律不能完全抚平情感,但如果纪录片能让观众理解‘过程’,那就比简单的结论更有意义。”
真实与伦理的边界
从新闻调查到纪录片创作,詹佳骏始终坚持真实与伦理的底线。他在拍摄时尽量保留同期声,少用解说词,让当事人自己开口,而不是用导演的语言替他们发声。
“我们不能为了煽情而剪辑他们的苦难。真正的尊重,是在镜头里让他们做回自己。”这句话,他一再强调。
坚持人文关怀的道路
对未来的创作方向,詹佳骏有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我知道,坚持人文关怀的纪录片很难,但这就是我想做的。如果影像能让一个残疾人多被理解一点,让一个家庭多一点耐心,那就够了。”
詹佳骏也希望把 AI 视频生成等新技术引入纪录片创作中。他的看法是:AI 不会削弱纪录片的真实性,只要被清楚标明,它反而能帮助观众更直观地理解某些无法拍摄的情境与历史瞬间。在他看来,真实性并不是影像的物理来源,而在于导演如何忠实地传递当事人的经历、情感与立场。
在《上班》中,是残疾人想证明“我能工作”;在《是》中,是申诉人渴望一个“我依然存在”的回应。两个看似无关的分集,指向的却是同一条社会命题:我们如何看待那些最容易被忽视的人?
詹佳骏把答案留给观众,但他的镜头已经给出了方向。纪录片不是终点,而是让公共记忆拥有温度的起点。

图说:《人生第一次》在河南残友基地拍摄

图说:《人生第二次》在最高检西区拍摄公开听证

图说:参加上海市教工影视协会学术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