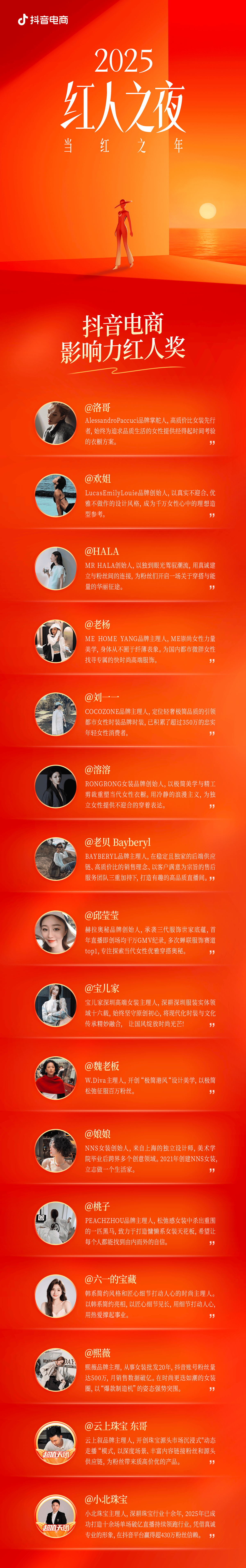—— 电影作曲家王立森专访
在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的画卷中,有一种声音不紧不慢地流淌着,仿佛从遥远的雪山、草原、戈壁滩飘来,又悄然融入银幕上情感的波澜中。王立森,这位从陕西走出的作曲家,以其深厚的民族音乐根基与电影语言的高度融合,在中国影坛写下了独特的一笔。
音乐的根,是从西部泥土中长出来的
出生于1979年的王立森,自小便沉浸在中国西部厚重的音乐氛围中。生活在秦腔世家,戏曲,民歌伴随着他的童年。1995年考入西安音乐学院附中,经历七年科班学习,2002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随后又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作曲。他的音乐之路没有刻意的铺设,更多是一种自然的生长,是对音乐和文化的直觉感知。
“我不追求一种风格,而是在感悟音乐背后的土地与人,”他曾这样说。
这种感悟,贯穿于他的代表作中。2019年,他为电影《远去的牧歌》创作配乐,作品获得第15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音乐提名;2021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音乐,再次获得该奖项第17届提名。而在2025年,他创作的电影音乐《巴扎喜事》也入围了上海合作组织电影节,标志着其在民族题材电影音乐领域持续稳定的影响力。
少数民族音乐与现代电影语言的碰撞
王立森的音乐创作有一个鲜明的特征:他并不单纯“使用”民族音乐,而是在“对话”民族音乐。他不复制民间旋律,而是捕捉它的动机,挖掘它的精神,再用现代电影音乐语言重新表达。
“民族音乐与现代电影音乐的碰撞,不是拼贴,而是融合,是情感上的通感。”王立森解释。
他的作品中有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等地区的传统乐器、人声,节奏与调式,同时通过电子音色、交响结构和氛围音乐,将传统意象注入现代叙事中。比如《远去的牧歌》中,他运用哈萨克音乐元素,不仅作为旋律配器主题,也渗透于整部影片的音乐结构中,与人物的内心变化共振。又比如《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更是融合了维吾尔族音乐的精华和动机,并不局限于原生态的复现,而是将其解构、再编织,成为电影情绪的有机组成。又比如《巴扎喜事》中将都塔尔与琵琶置于同样主奏地位,把都塔尔作为一件“真正的”弹拨乐器使用。这部作品节奏更为轻盈,但风格中即有史诗,又有流行,即能爵士,又能摇滚,却依然流露出他对地域文化的尊重与热爱。
用音乐讲述被忽略的故事
电影中的声音,不只是背景,更是叙述者。王立森擅长用音乐为角色“说话”——尤其是那些不善言辞、深藏故事的人。他相信,一部好的民族题材电影配乐,不应只是地方色彩的修饰,更要成为世界不同民族心灵的桥梁。
正因如此,他常常深入拍摄地采风,与当地的歌者、乐手,牧人、工匠交谈,记录他们的声音与生活。他用音乐,搭建起从原野到城市,从民族到世界的通道。
“音乐是情感的方言,好的电影音乐是跨文化的语言。”
音乐人,也是文化的桥梁
如今,王立森定居在北京,但他始终将创作的触角延伸至祖国的边疆与民族的土壤。他希望未来能进一步推动中国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流行音乐、甚至爵士等风格的跨界合作,打造属于中国的世界音乐声音。
王立森说,他常常会在录音棚工作到深夜,然后独自一人驾车穿过北京的街头。这座城市的夜,有霓虹,也有沉静,有人群,也有回响。
“民族音乐不是素材,而是性格。”“我希望我写的音乐,是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
于是我们知道,他所追寻的,其实从未远离。它一直在他体内,在他的旋律里,在那一段段没有歌词的音乐中。
他相信,在世界的语境下,民族音乐不是地方性的标签,而是文化身份的核心。
他不满足于“民族风”的外衣,更想深入到文化的肌理。他的作品往往没有高亢的主题旋律,却令人难忘于细微之间。他擅长留白,用空间感与呼吸感营造情绪的涟漪。
“有时候我写的不是一首歌,而是一段沉默。”王立森说
后记:听,风的方向
王立森的音乐,是一条静水深流的路径。他用音符勾勒远方的牧歌,也编织今日的心灵。他的创作,不仅在述说少数民族的故事,更是在回答一个属于当代中国音乐人的命题:我们如何在全球化中,守住自己的声音,又把它唱给世界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