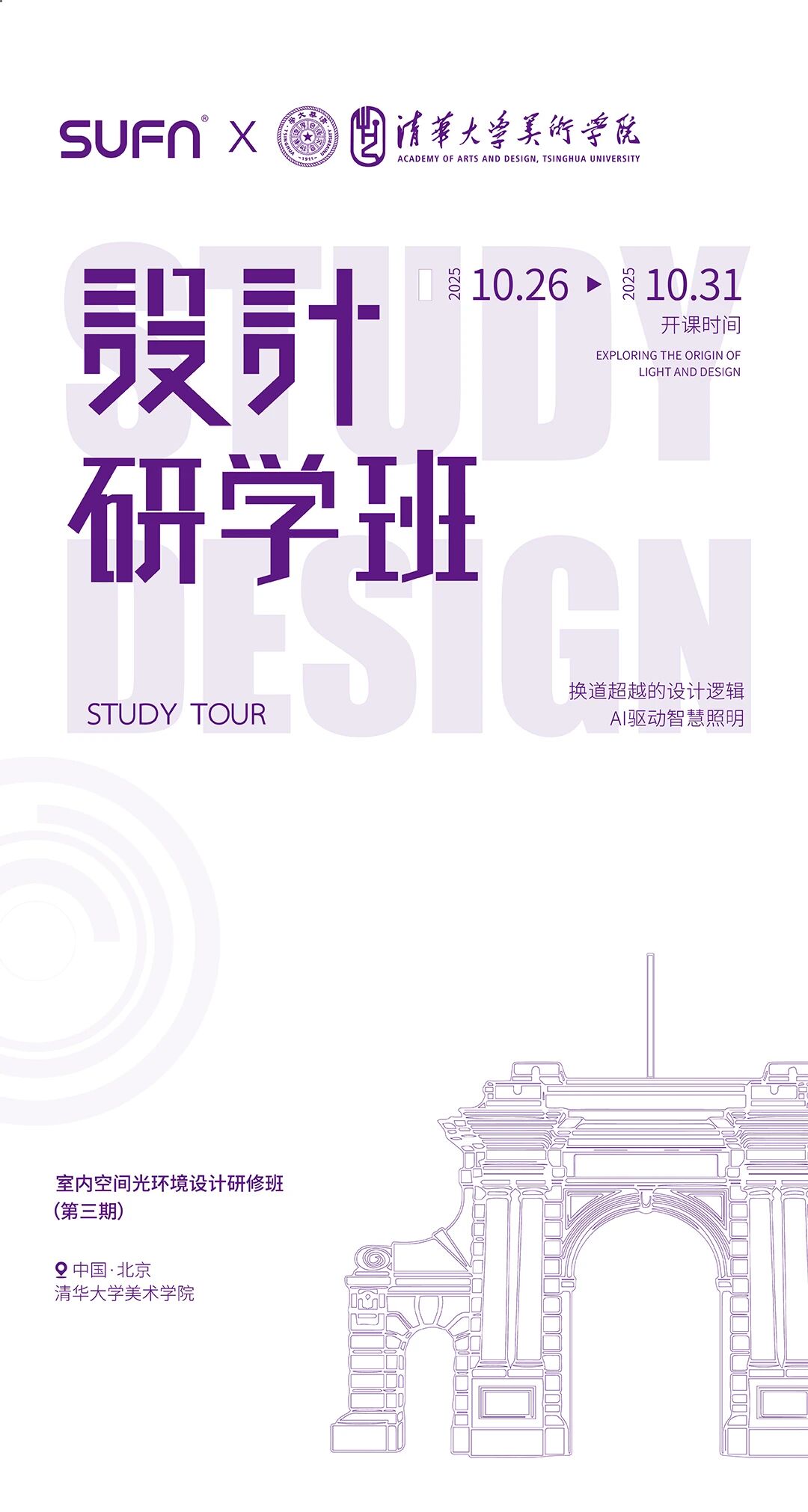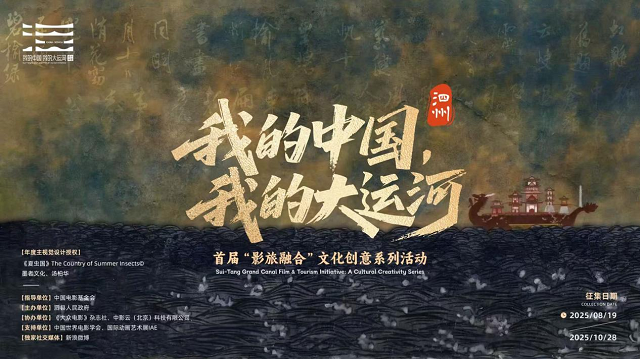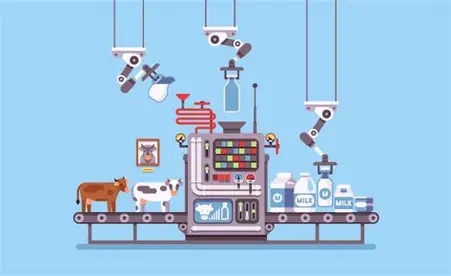最先要赴的约—-在“时影·影像艺术中心联展”区,我的四幅作品就在那里参展。四幅作品并排挂在墙上,像四个沉默的叙事者,守着“看见·世界”这个主题,等待懂它的人驻足欣赏。

站定的那一刻,镜头里的光影突然活了过来。“叩响藏地之门”的经幡还在风里翻卷,西藏海拔四千多米的阳光,仿佛还晒在肩头。红墙下停着的新能源汽车,车身上落着几缕经幡的影子——原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不是抽象的词,而是西藏几十年的真实写照,是古老与新生在同一帧画面里的温柔相拥,也体现在女主角的微笑里。

“熊猫食竹”的画面总带着暖意。圆滚滚的家伙抱着竹子啃得认真,饲养员胸前的工作牌隐约可见“出访交流纪念”的字样。这团毛茸茸的黑白,曾在不同国家的动物园里,被不同语言的惊叹包裹。原来和平可以这样具体,带着竹叶的清香,藏在跨越山海的凝望里。

目光落在“林间鹿影”与“麦间丽影”上时,呼吸会轻轻顿一下。照片里的乌克兰姑娘,眉眼像多瑙河的波,笑起来时,发梢都缠着阳光。

那是战争爆发前,她作为文化使者来中国,经朋友牵线,我们在郊外的树林与麦田里拍摄了半天。她是国家功勋话剧演员,也是世界级模特,镜头里的她,时而化作林间精灵,时而变作麦田诗人。

可如今,硝烟漫过三年,新闻里的碎片拼凑不出她的模样。她还能在舞台上舒展吗?还能遇见那样透亮的蓝天吗?照片里的笑那么亮,看久了,眼眶会悄悄发热——原来“看见世界”,既要收纳美好,也要接住美好碎落时的疼,还要把“愿硝烟散尽”的祈愿,缝进每一道光影里。

正被这些念头缠裹着,一道身影停在了作品前。金发姑娘,睫毛像蝶翼,指着照片又指着我,语速轻快地说着什么,眼里闪着雀跃的光。我正窘迫,旁边的年轻翻译笑着解围:“老师,这位是西班牙的摄影师兼策展人。她说中国摄影展上,少见专门为欧洲女性定格的镜头,觉得您的目光很特别。还说,看您满头白发,是中国摄影界的‘大爷’呢。”

我忙摆手,拉过翻译:“可不敢当。中国摄影界的‘大爷’,是那些拿过金像奖的大师。我呀,只是个追着光影跑的老头子。”

翻译转述后,她忽然朗声笑起来,像风吹过铜铃。又一阵低语后,翻译说:“她讲,您的作品与‘看见·世界’太契合了。她想邀请您去西班牙参展,让更多人透过您的镜头,看见更辽阔的世界。”

末了,翻译补充:“她想邀您到外面拍几张合影。”

我笑着应了。并肩站在展馆外的大树下,快门按下时,忽然觉得奇妙——前一刻还在照片里惦念远方的人和事,这一刻,远方的善意已轻轻叩门。原来镜头真的能搭起桥,让不同语言的心跳,在“看见”与“被看见”里,慢慢同频。

风穿过庭院,带着桂花香的余韵。原来所谓“与世界接轨”,或许就是这样:你认真记录着世界的模样,世界便会循着光影,悄悄向你走来。(袁浩 文/图)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