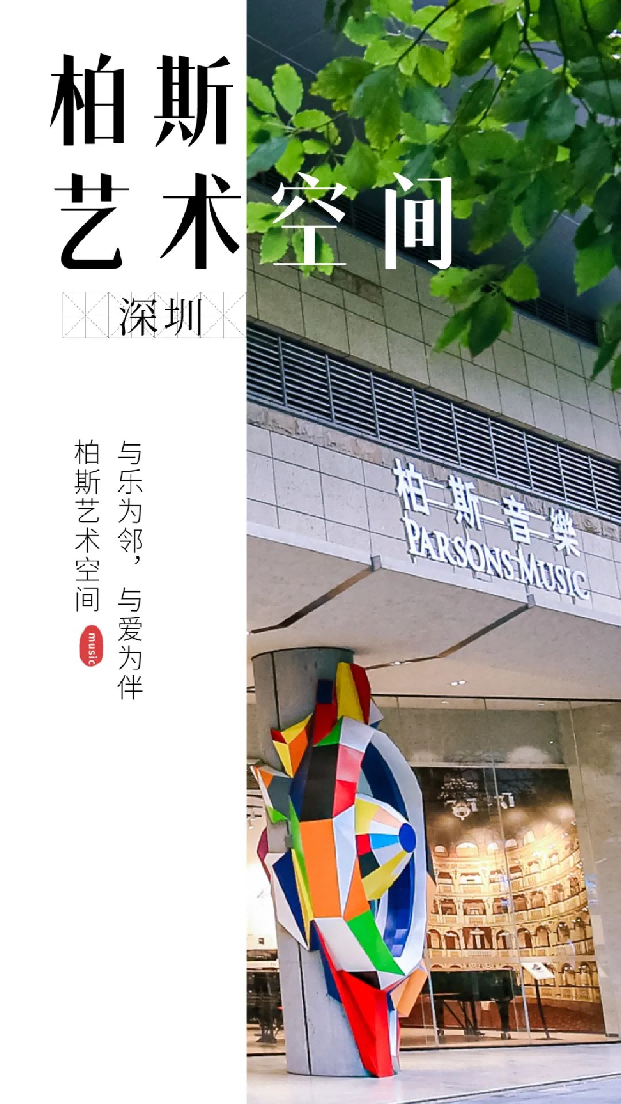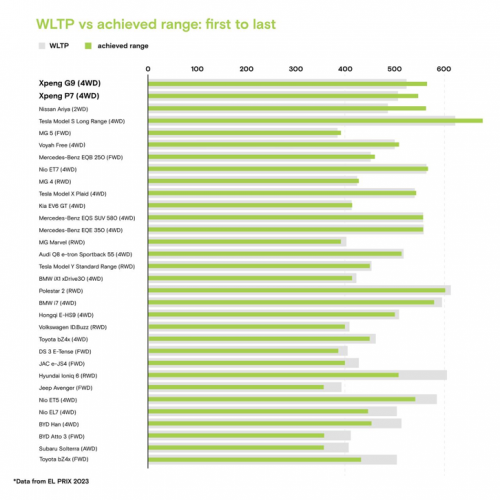【艺术简历】
高明宇,教授,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研究方向:中国画大写意花鸟
现任职务:现任东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公共艺术教学部系主任、兼职于哈尔滨青年画院副院长。
2000年—2019年,在国家级、省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多幅作品被国内外专业机构收藏。
主编过两本专业教材、四本个人画集。
2000年至今获得国家奖项七项;省市级奖项十八项。
主持省级课题一项、 校级课题一项、省级在研一项。

花鸟画的意趣表现
高明宇
就中国花鸟而言,自然和鸟禽是其主要的表现对象,广义上说,草虫、鳞介、鞍马以及走兽都包括在内。对于花鸟画的创作来说,是自然的人化过程,画家赋予了作品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又寄予了个体和对家国的无限情思。如果说,花鸟画的“情趣”偏重情感;“理趣”侧重哲理;那么“意趣”就是思想、志趣。

通常认为,山水画营造意境;人物画讲求神韵;而花鸟画表现的正是情趣。实则不然,可以说,情趣表现在中国文学、艺术审美、社会文化等方面,不是流于表面,而是深深地渗透、嵌入其中。宋元之际的词人张炎在他的词论专著《词源》中,就有《意趣》这一部分,其云:“词以意为主,不要蹈袭前人语意。”他用苏轼等人的词佐证之,又说“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这里所说的“意趣”是从内容和创作来说的,也就是立意之趣。明代的戏剧家汤显祖在《答吕姜山》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这句话是针对重曲律忽视情感的吴江派而言,汤显祖表明反对戏曲创作拘泥“曲律”,而提倡“曲意”。《宋书·萧惠开传》有:“意趣与人多不同。”是指人物的品藻,此为论人的旨趣、志向。北宋的书画家米芾在《论山水画》中说:“董源雾景横披全幅,山骨隐显,林梢出没,意趣高古。”可说,意趣并不是花鸟画特有的概念,而是在中国通用的美学范畴。

中国花鸟画的意趣在思想层面,表现为情理、思想、趣味上审美的合一。就其思想根源,深受“自然比德”“禽兽比德”思想的影响,换句话来说,中国人审美是离不开道德的评价。在中国的史前社会原始初民,一方面,对外部世界开始了模仿和认识,这成为早期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太昊师蜘蛛而结网”“人类向禽兽学习,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学会了歌唱”。模仿自然是人类生存的重要方式,花鸟早已进入了人类的视野,在我国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的花纹和岩画上可以看到动物的形象和植物的花纹,可以推想我们的祖先改造自然,取得动物的皮毛、植物的果实解决生活需要后,将它们的形象装饰在生活器皿上,既表达胜利的喜悦又美化了生活,对形式寄予了人类的意味。另一方面,在与自然界不断的互动进程中及其和他人的交往中,个体意识不断地在集体中形成,图腾崇拜融入了初民的自我意识和远古民族的集体制形式,图腾崇拜由植物崇拜走向动物崇拜,意味着人类的主题能力不断提升,蛙纹和鱼纹由早期的具象不断发展到抽象,作为生殖崇拜的形式,体现了人类的生生之德。工具的发明也不断地融入其中,自然不断地人化。

夏、商、周三代以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甲骨和青铜器上可一看到许多形象突出概括的虫、鸟、草木、动物文字和花纹,它们由图腾的崇拜变为了国族的象征;随着“禽兽比德”思想的不断完善,花鸟、松柏、动物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图腾的崇拜,而被赋予了道德观念,如乌鸦反哺、松柏之后凋。同时,器物上的花纹在有了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外,还可以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具有了认识论上的意义。
有汉以来,汉初统治者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外黄老,内儒法,始终缠绕着功利主义美学观,随之而来谶纬大兴,笼罩着神秘主义气息,但艺术却不断地生活化,草木、花鸟、走兽曾渗透到漆器、瓦当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魏晋以来,自然的地位不断提高,虽然花鸟画摆脱了它的装饰地位,进入了供人欣赏的画卷,但它和山水画一样,只是做人物画的配景应用,如《洛神赋图》中的花鸟形象只在暗中陪衬。五代佚名画家创作的《丹枫呦鹿图》中,鹿的部分用写实的笔法,甚至有一点体积和光影的表现,先淡勾轮廓,再用墨细腻渲染,近于没骨法。秋天的树林,从深红到淡青,还是有装饰的痕迹,树叶使用了勾勒填充法,厚涂在铅白上,是轻淡的青红,显现出盛开的树木的特征,而“鹿鸣”以仁求其群,有文化传统的渊源。处于边缘的后蜀和南唐相对和平安定,继承了唐代的写生传统,出现了黄荃富贵和徐熙野逸的不同画风,为宋代的花鸟画成熟奠定了基础。北宋《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云:“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本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诗文在表情达意上互为表里,而宋代的花鸟画是建立在写生的基础上,意趣通过色彩赋形、结构营设中表现出来。有宋以来,随着文人花鸟画和大写意花鸟画的不断形成,尤其是南宋到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外族入侵,流民、遗民心态不断融入到花鸟画的意趣中,花鸟画的写意性、意趣性更为强烈。到了近现代,金石、西方绘画因素等都遇合其中,大写意画鸟得到确立与发展。可以说,意趣是主观的思想与趣味、真趣、天趣、生趣、奇趣、逸趣的契合,更是笔墨精神。

我个人对意趣的理解并不仅停留在思想和历史层面,也表达在画家的个性语言上。我在绘画创作和思想上深受高卉民老师的影响,而高卉民是沿着吴昌硕—潘天寿—张立辰的大写意绘画传统,深及中国文化的最深处,又将人生的苦涩和野趣融入到自己的绘画之中,并探索出了北方荒寒意境的笔墨表现方式。其艺术观念与绘画风格通过言传身教、艺术展览与学术杂志的研究与报道等传播方式,在黑龙江美术高校范围内形成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同时也因其数十年的花鸟画教学,以师生相授的方式,由追随其画法与理念的师生群体联结与持续传承,形成了画法相对一致的、稳定的、带有学派性质的花鸟画群体风格。我个人在的学术思想与艺术主张,秉承在传统题材基础上,选择传统花鸟画中很少涉猎的表现题材——黑龙江域内北方生态环境中独有的、却被传统花鸟画忽略的动物、植物、花草等形象,如田鼠、刺猬、黑熊、野狐、啄木鸟、鹌鹑、玉米、黄豆、谷子、白菜、大蒜、向日葵、蒲公英、蒲棒、山菇娘、芦苇、水葱、荆条、野菊、残荷、衰草、落叶、冻枝、寒林、冰雪等。我以北方荒寒作为审美方式的绘画方向和创作观念,将荒寒之美,荒寒之境与文人的意趣融汇在一起,并追寻独树一帜的野情、野意、野味、野境。

我在技法上对花鸟画的意趣表现在,以多种无规则笔墨变化表达缩水、干枯的植物形态,用以呈现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残缺、萧索、枯败、荒凉等地域特征。高卉民在线条的画法上,着意打破骨法用笔对于形体塑造的规律性,如以提按顿挫的不规则运用突出的枝条粗细变化,以顺逆与速度变化的结合塑造线条虚实差异,以转折方式无规律形成的线的方向性变化,以及侧逆散聚等笔锋角度差异形成的线条质感变化。为规避生宣纸特殊晕渲和渗化作用及毛笔柔软特质造成的笔触相互融合、重叠和渗透的媒介特性,对于笔的力道、速度、干湿等方面进行了反复研究,探寻笔锋顺逆、正侧、平斜等位置上同时无规则变化,并加入干湿清焦的对比反差以塑造出随机变化的形态,将多种对比变化性因素融入线条运用之中,侧重用线的松、活、毛、涩,以表达黑龙江荒寒植物及冰雪覆盖所形成的无规律的形态特质,并强化笔墨干湿对比对地域冻枝、荒草及凋叶质感的烘托。同时将形态的结构与质感的表现浓缩于线的变化之间,使绘画形成视觉上的丰富质感变化,笔意韵味之间塑造了作品“老辣劲快”的豪迈气势,并不追逐意趣灵动之美。在对北方意象的表达上,确立了以冻枝的线性特质为主线,以墨团的凝重或枯焦为残叶、冻土及动物形态的主体表现方法,以统一色彩的区分为笔墨塑造的方式。

大写意画法较为考验画家造型提炼的能力,形态的准确与生动性是大写意花鸟引人入胜的审美趣味所在。既有笔势变化又包含形态特征,完全取决于笔法对于结构与神态的包含程度。要将禽鸟结构融入笔法,形成“一笔一结构”的表现方式,同时为了强化禽鸟的情感特征,对禽鸟的头部比例与轮廓进行变形与夸张,着意突出眼部与喙的特点。这种禽鸟面部特征的塑造,几乎在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中均有呈现,成为绘画风格的标志性造型符号。而形态概括方式的个性化构造思维及构成理念的融入,在构图与画面结构上呈现出区别于传统写意花鸟画的个性化的意趣表达。

明代汤显祖在《与宜伶罗章二》中说:“《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愿做的意趣大不相同。”其实在花鸟画中一两笔就是精微,笔触拟趣,也是花鸟画在统一基础上的意趣表达,也就是张立辰先生所说的,“始知真放本精微”,一语道破了中国画创作的机要。又要把个人的意趣与时代的精神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