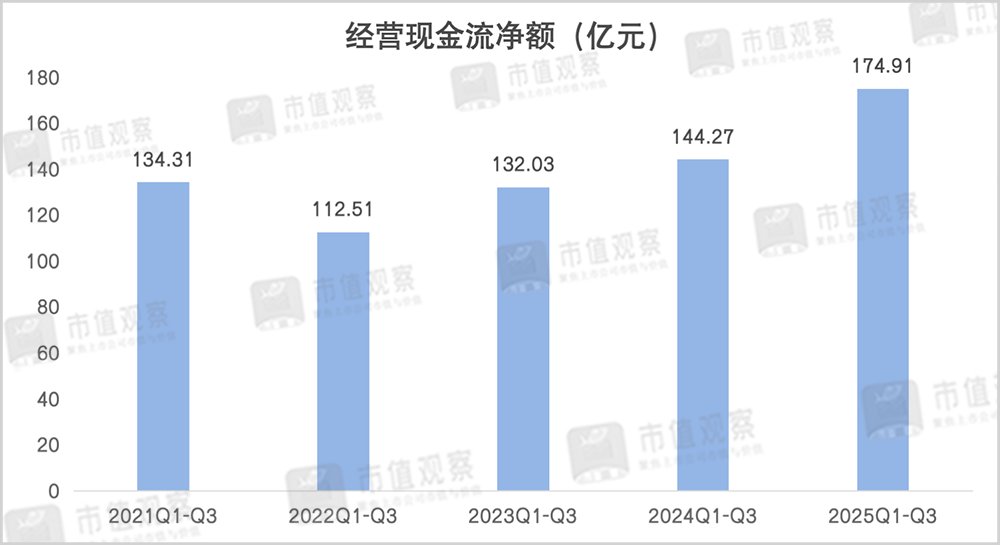——文/王蔚伟 (美术评论家)
在当代中国花鸟画演进脉络中,王杰克逊(原名王永华)先生的《虾》系列作品,恰似一座横跨传统与现代的虹桥,既承载着齐派水墨的基因密码,又融入了全球化时代的视觉语法。这幅被多国政要珍藏的《虾》,绝非简单的生物摹写,而是艺术家以毕生修为对水墨精神所作的当代诠释。
观其用笔,可见白石老人“以书入画”的精髓——虾躯的勾勒取篆籀笔意,节节相衔处暗含“无垂不缩”的书写法则。尤见功力的是虾须的处理:中锋行笔若吴带当风,绵长而具弹性,在疾徐顿挫间构建起画面的音乐性节奏。更难得者,王永华在传统“破墨法”基础上发展出“颤笔皴擦”,通过笔锋的微妙震荡,将虾壳在清水中的通透质感转化为墨韵的视觉交响。
《虾》的墨色层次堪称一部微缩的水墨哲学。王永华画家以焦墨点睛,淡墨写躯,通过水分与宣纸的呼吸作用,营造出“墨分七彩”的光效幻觉。虾体腹部的水痕处理尤见匠心,那并非物理性的留白,而是引书法“飞白”笔意入画,使虚空成为构图的积极要素。这种对负空间的创造性运用,恰与迈克尔·杰克逊舞蹈中的瞬时定格形成跨艺术门类的共鸣。
王永华的虾既超越了解剖学的局限,又突破了写意画的程式。他敏锐捕捉虾体在游动时的“S”形张力结构,将太极推手的缠丝劲转化为视觉动势。虾钳的开合已非生物本能,而是被赋予“执虚如盈”的哲学意味,那弓身欲跃的瞬间,既是对齐白石“似与不似”理论的实践,又与当代视觉心理学中的“知觉完形”暗合。
这些游弋在各国政要厅堂的水墨精灵,实则是文化外交的轻盈使者。王永华巧妙地将“虾”的汉语谐音“哈”的欢愉意象融入创作,使观者在解码东方美学时,自然领会“和谐共生”的东方智慧。这种将传统花鸟画注入国际语境的尝试,恰与其联合国和平大使的身份形成互文,让水墨艺术成为文明对话的通用语法。在这幅《虾》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画家对先师笔意的深刻理解,更是将个人生命体验转化为时代视觉符号的创造勇气。当那些透明的甲壳在纸面呼吸,当劲健的须髯划破时空,王永华证明了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在全球化时代的鲜活生命力——这既是向传统的深情回眸,更是对未来的敏锐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