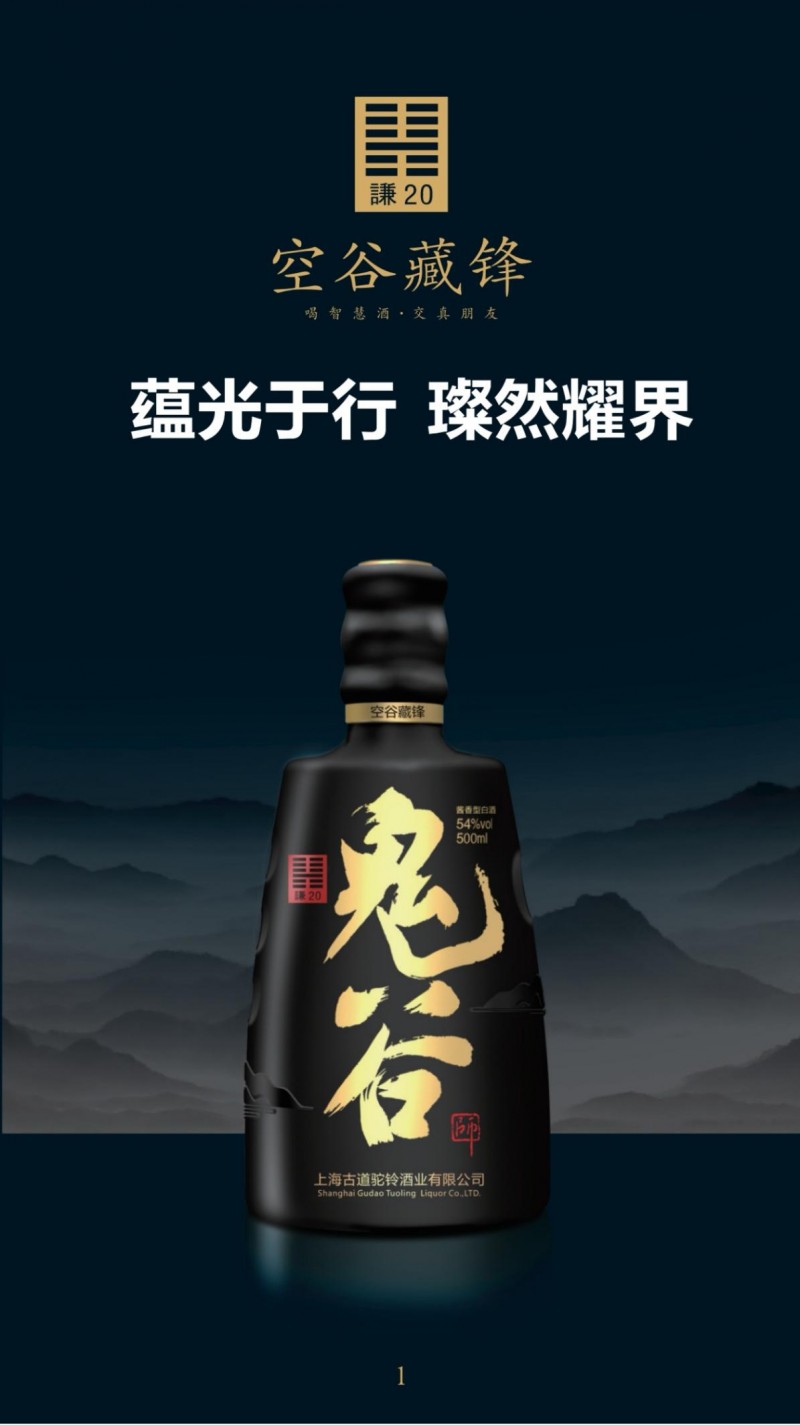2025年作为“双碳”战略攻坚年,中国碳达峰经济政策迎来里程碑式突破。截至2025年5月9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到6.4亿吨,累计成交额为441.3亿元。随着混合碳定价体系建立、电力市场化改革、绿色金融创新等协同发力,中国正以制度创新重塑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近日,浙江工商大学张崇辉教授围绕碳达峰经济政策,指出我国正在改写全球气候治理规则。但是,随着碳达峰目标纵深推进转入关键阶段,中国碳达峰经济政策体系正经历系统性重构。为了实现从技术突破到制度输出,需要理清以下三个方面的底层逻辑。
顶层设计:破解政策协同的“三元悖论”
当前碳达峰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减排刚性约束、经济平稳运行与区域公平发展的三重目标。破局核心矛盾,要正确理解碳税的累退性。研究发现,在2025年达峰情景下,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工业产值损失比例分别为2.84%、4.02%、5.21%,即征收碳税对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造成的经济负担更重,将扩大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为减弱碳税累退性对区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中西部地区在征收碳税时,可以先设置较低的税率,并依据地区经济发展实际状况逐步提高税率。
这种非对称政策工具箱,既避免了“一刀切”对欠发达地区的冲击,又为技术迭代争取缓冲期。但需警惕的是,区域补偿基金尚未完全覆盖产业转移的隐性成本,可能催生新的“低碳洼地”。
市场机制:价格信号重构产业逻辑
碳税与电力改革的本质,是通过价格信号倒逼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研究发现,碳价每上涨10元,可能会导致重工业成本陡增1.5%-2%,这种“创造性破坏”正在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代际更替。为加速推进碳达峰目标,参照浙江省经验,依据企业评级实施差异化定价。比如,可通过对D类企业实施惩罚性阶梯电价,差别化电价措施可以在倒逼D类企业转型。同时,对A、B、C类企业形成潜在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工业用电效率,降低用电需求和用电成本。然而,这一措施也会对部分产业的均衡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阶梯式电价与绿电交易形成的“双向调节”机制,既通过惩罚性定价压缩落后产能生存空间,又会以绿电溢价引导资本向新能源聚集。这种“破立并举”的调控艺术,体现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优势,但也考验着政策制定者对市场敏感度的把控能力。
绿色金融:从资金配置到生态重构
绿色金融正经历从单一工具向系统生态的范式跃迁,其核心逻辑已突破传统信贷资源配置的线性思维,转向构建覆盖“定价-交易-风控-治理”的全链条生态体系。
在环境风险内部化机制驱动下,绿色金融通过气候相关财务披露(TCFD)框架重塑资产估值模型,将碳成本、生物多样性损益等外部性要素纳入资本定价内核,推动金融市场形成环境风险定价的“新锚点”。工具创新层面,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衍生品等结构性产品,通过“绩效对赌”机制将融资成本与企业减排目标动态绑定,实现从“筛选式投资”到“赋能式参与”的跨越。政策协同维度,“央行-监管-财政”三位一体框架下,差别化准备金率、绿色资产风险权重调整等宏观审慎工具,与碳账户体系、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形成制度合力,引导私人资本向低碳领域规模性迁移。
这一生态化进程的本质,是通过金融工具的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的深度耦合,将碳中和目标转化为可定价、可交易、可迭代的经济系统参数,最终实现环境价值与金融价值的范式统一,为全球经济低碳转型注入可持续的系统动力。
最后,张崇辉教授指出碳达峰经济政策的实施会面临制度红利与风险并存的挑战。他表示,当前政策体系虽初见成效,但深层矛盾仍在累积。绿色信贷快速增长的背后,中部地区“环保评级与融资成本倒挂”现象值得警惕;个人碳账户6亿用户的庞大规模,尚未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端减排动力。更关键的是,当政策驱动转向市场自觉时,如何避免“补贴退坡-技术断档”的转型陷阱?这要求政策设计必须预留足够的弹性空间,在“政府之手”与“市场之力”的动态平衡中,走出一条兼顾效率与韧性的中国式低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