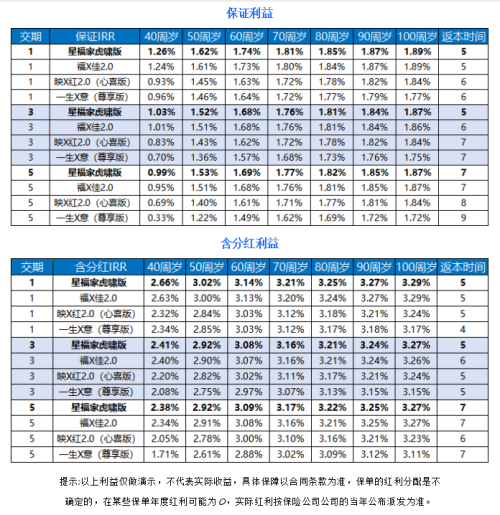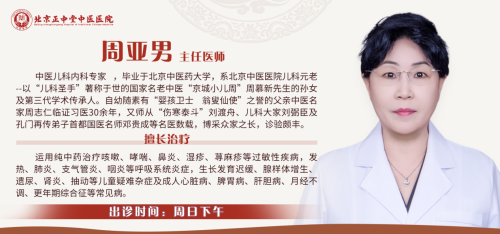作为一名艺术史学者,我会用很多时间来观察艺术作品,进行相关的分析与写作,我也希望可以启发他人做同样的事情。
今天,我在观赏公元三世纪的犍陀罗佛像时,回忆起了去年夏天在青海省囊谦藏区的那些时光。当时我和六岁的儿子一路旅行到了青海,去参观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的赞普博物馆、民宿和艺术驻留地,也逃离了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的江南酷暑。赞普博物馆和其配套建筑临近青海省囊谦县县城,毗邻佛学院,四周群山围绕,海拔3700米高度的空气中有着超凡飘渺的氛围。
2024 | 晨雾中的赞普博物馆
我第一次到囊谦也是因为艺术。2017年3月,我来到这里见证了赵要的巨幅大地艺术作品《精神高于一切》(Spirit Above All),该作品装置在摩耶寺外附近的山坡上。这些创造性行为的背后则凝聚了乔美仁波切——一位佛教老师、电影导演和创业者的心血与智慧,他的悲心远见孕育了开创性的交流通道,使得囊谦与北京、上海和尽未来际产生了直接的联系。2019年,乔美邀请北京的亼建筑为彼时容纳了宿舍和文化艺术品收藏的传统建筑设计扩建方案,其成果是一座融合了传统西藏元素 (当地垒石工艺) 与中国城市常见本土极简风格 (钢与玻璃结构) 的建筑群,带有几何设计的彩绘门楣和悬挂的毯子点缀着新颖而利落的建筑线条,并创造了一种新颖的美学和功能混合体。
II艺术家现场创作:无上之心
2017 | 赵要作品《精神高于一切》
原先的宿舍改建成了民宿客房用来容纳大量涌入青海的游客;而从前收藏民俗艺术品与器物的建筑扩建后成为了一座获得建筑奖项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当地藏族人管理所有事务,他们轻松而又善解人意地照顾我们的需求。每天他们都会运用刚刚学来的技术在高海拔的环境下烘焙欧式面包,并用当地采摘的香草豆和囊谦红盐等食材加以创新。创新性的场地营造以及人与人的联结感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日常。
| 刚出炉的酥油面包
建筑作为框架
山,和建构环境一样,会塑造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的经验,我发现了山里面的空间结构是如此有力,尤其是作为隐退处。赞普博物馆的民宿列于长廊之侧,形制相仿,毗邻盥洗室和厨房,并连通了公共空间,二层阁楼是一个图书馆,图书馆有一个开阔的露台,可以俯瞰佛学院及简朴的宿舍。公共区域里摇曳着赭红色僧袍的身影,与旅客、当地人泯然一体,空气里还飘荡着新出炉的面包香气。这里的气氛如此亲切而有魅力,我的儿子甚至有了个习惯,他总是指向人群问我,“他们也是我们家的一部分吗?” 我和他说,“我猜他们是,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家人。”
2008 | 一期建筑始建于2008年
| 赞普图书馆窗景
赞普博物馆高大的木门通向一个与客房连成一体的庭院,庭院中央的展厅采用白盒子式的设计,层高很高;展厅里陈列着国家一级唐卡画师为赞普博物馆创作的唐卡画作;艺术家赵要的 《精神高于一切 》系列作品中的玛尼石堆就并列陈放在地板上。阳光穿过落地玻璃窗,照射着展厅内的裸露砖墙。展厅的隔壁是为驻留艺术家们准备的工作室,另有一个木质楼梯通往 “玻璃盒子” ——它是整个建筑群结构和精神的核心。
| 赞普博物馆内的作品陈列《爱》
“玻璃盒子” 如其名所述:一个由长方形的立方体,玻璃窗格悬挂在黑色金属桁架之间,可将外面的群山尽收眼底。从外部看,它们的镜面栖息在白色垒石建筑之上,极具未来感,就像一艘隐形飞艇,通过反射天空的状态和色调而变得无影无踪。从室内看,“玻璃盒子” 营造了一个多功能空间,可以用于讲座、瑜伽、表演、骑行、小憩——它是空的、不确定的,仿佛一个钵盂邀请我们进行开放多元的内容填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玻璃立方体外令人惊叹的景观是动态的和绝对的,它不需要任何添附,只需我们的专注。坐在 “玻璃盒子” 内,它结构上的材料性溶入了对面的群山之中,我们被赐予了当下的自由,摆脱了建构环境的束缚。我们可以一边欣赏风景,一边被庇护在建筑内部。如果将 “玻璃盒子” 窗框内的这幅风景图像作为一件艺术品,它一定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匿名,《无题》,日期不详,各种地质元素” ,它极具当代感,因为它是鲜活的、和合的、当下的和开放的。
| “玻璃盒子” 在夜晚熠熠生辉
这里的人更像空间的守护者和看管者,而非所有者或权利人。在这个赞普 的“大家庭” 里,没有人会限制你如何使用或占有这个空间——他们甚至多次责备我试图限制我儿子的行为和好奇心。“玻璃盒子” 就像心理学上所说的,为你爱的人 “留出空间” 的实体版,周围的群山也会聆听我们。摆脱规矩和具体框架的束缚后,我们的激素水平比在内地城市时下降了,我们开始放松,重新积聚自己的能量和创造潜力。这些景色使我们感到谦卑,并提醒我们,“大自然” 会不断超越我们所创造的一切,但她是一位如此出色的老师,以至于在 “玻璃盒子” 里,面对这件杰作时感到灵感涌现,并鼓起勇气去尝试。
| 禅修室一隅
注意力经济
作为一名翻译和作家,我并不制造事物而是创造想法。艺术和物质文化对我的工作来说至关重要,但我并不希望通过商品来增强人类的存在感。与此相反,我想要强调的是物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拓展我们的人类体验和认知,类似于简·本内特 (美国哲学家) ,布鲁诺·拉图尔 (法国哲学家) ,或伊恩·霍德 (英国考古学家) 所描述的那样。犍陀罗式佛像通过将希腊特色融入佛教造像,实现了东西方的融合,而我的工作尝试通过寻找艺术所讲述的故事来缝合我们的文化鸿沟。艺术还有哪些新的方式可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呢?
| 由30个牦牛角创作的户外装置作品 :融为一体的纯洁世界
我们的注意力具有货币性价值,软件开发者竞相通过我们的小手机屏幕来捕捉我们的注意力,在这个平行维度里,我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消费能力。注意力是一种无形的有限资源;在信息过度饱和的时代,它因稀缺而变得弥足珍贵。
青海高原的山脉瞬间捕捉并保有了我们的注意力,这种震撼感令我们反思,并短暂地获得自我解脱。这就是游客来到这儿的原因。从历史上看,山是隐居的处所,进山是一段个人心路的重要部分。从十世纪巨然和关仝的山水画,到清初石涛等游方僧侣画家的画册, 这一点在世界艺术史中有详尽的记载。更近代的在美国艺术中,19世纪哈得逊学院画家的风景画也受到了爱默生和梭罗超验主义写作的启发。随着我们对自然的专注和全然的注意力越来越少,与纯粹未经修饰的大自然共处的机会也变得愈加珍贵。类似囊谦和赞普这样的地方提供了与至臻至美共处的珍贵体验,其价值不证自明。人不需要相信什么智性设计,就能被这矿物山脉的多层笔触所构成的景观所感动,这些笔触展现了与青藏高原一样广袤深远的地质时间。
| 冬天的牦牛
守恒定律和可逆原理
在其数百件最近几个世纪的编目藏品中,赞普博物馆如今藏有了一件杰作:这片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时代的快速发展确实对环境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然而近三年三江源地区的环境保护亦取得了显著成效。
七年前,我来这里的道路还很艰难,但基础设施的改善为当地人带来很多机会和经济发展。然而,如何确保这些财富的持久性呢?矛盾的是,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破坏了美丽的景观、原始而人烟稀少的美感,其固有价值将随之下降。与注意力经济的前提类似,有限资源因稀缺而增值,而这种类型的自然景观正在整个中国逐渐消失,从而提升了 “玻璃盒子” 内景观的固有价值。
城市居民前往青海,是为了寻找高原风景所带来的自由感和内心的平静。他们来到此地,是为了体验奇迹。然而,正如中国绘画鉴赏家和保护者对古代丝绸手卷画上的风景所言:观一回,毁一回。卷轴的展开和卷起的动作不可避免地会侵蚀表面的颜料,使观看本身成为一种破坏行为。我们如何才能尽量减少因观看而造成的破坏呢?
| 博物馆对面山坡上的牦牛
为了建立旅游业的长期生命力,青海的自然美景——那幅被玻璃立方体框起来的 “山水画” 应该得到保护。正如博物馆把最珍贵的画作用玻璃保护起来一样,“玻璃立方体” 也在我们这些观赏者和未经破坏的自然风景之间放置了一层玻璃。它提醒我们,尽管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如果这块 “画布” 受到破坏,居民将失去最宝贵的资源。那么,我们如何转而思考能够在不破坏这块 “画布”的前提下提供发展机会的策略呢?赞普驻留项目旨在吸引艺术家和有创意的思想者来到这里,激发他们从这片土地获得灵感的愿望,并谋划创新的方法,为当地人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我的建议延续了 “将景观视为艺术作品的隐喻”,我主张采用艺术品收藏管理和保护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可逆性。这意味着:对艺术品的每一次人为干预、改动或添加都必须是可逆的。每一个行为都必须能够撤销,不允许永久性的添加。
| 雪山上的岩羊
极简主义的奢华
如果不是持久性的发展可能更像一种工程体验,而不是一个体系。可以采用哪些传统方法或临时、短暂的建造方式来取代混凝土建筑?这些都能展示传统和当地文化,并吸引国际游客,而可持续旅游业已被证明具有消费者吸引力。虽然深圳、西安和上海的豪华城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常设有艺术博物馆,但在这里,唯一令人向往的邻居是牦牛、雪豹和静默的佛塔。
| 博物馆外徘徊的公牦牛
| 艺术家 Michela Martello 在博物馆驻留期间的作品
附近新建成的 “盐文化博物馆 ” 成功展示了当地艺术家与商业模式的创新融合。他们优先考虑往往被忽视的当地艺术家和企业家群体,并让他们参与其中;其结果是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和博物馆展示,以及盐疗的融入。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游客和国际游客被吸引到与文化相关的景点。更重要的是,这种地方建设方式激发了人们对地方的自豪感。保护资源,将塑造游客体验的权力交到当地人手中,这可能是一种思维转变,但最终将获得最大的回报。
2024 | 囊谦红盐文化体验馆外观
几个月后,我们回到美国郊区的家中,过着平常的生活,处于你所习惯的平均海拔,我儿子突然问起了囊谦: “但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在哪里买东西?”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商店不见了,我们疯狂的消费被驯服了。我们被自己拯救了。
再回想一下艺术史证明的另一个哲学真理:“空白的画布” 并不总是意味着画笔来涂抹或搭建建筑。宋代的禅宗绘画和 1960-70 年代的美国极简主义都验证了留白的价值:有时缺失才是完整的。
本文作者:Lee AMBROZY | 安静
安静是一位作家、翻译家、艺术史学家和策展人,专门研究中国艺术和考古学。她编写了数本艺术家画册和出版物,在美国及中国各地授课和演讲,并与中国各地包括台湾的画廊和博物馆合作。她曾担任《艺术论坛》中英文网站的编辑,也是《白立方内外 ARTFORUM 当代艺术评论50年》的主编(三联书店,2017) 。她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班学汉语,并且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论文的主题为毛爷爷时代对传统水墨画的民族主义运用,目前在纽约大学的美术史学院完成她的博士论文,研究自然界图像在唐宋绘画中的功效与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