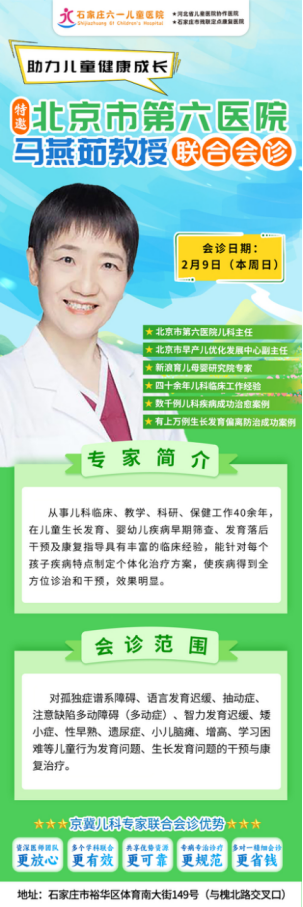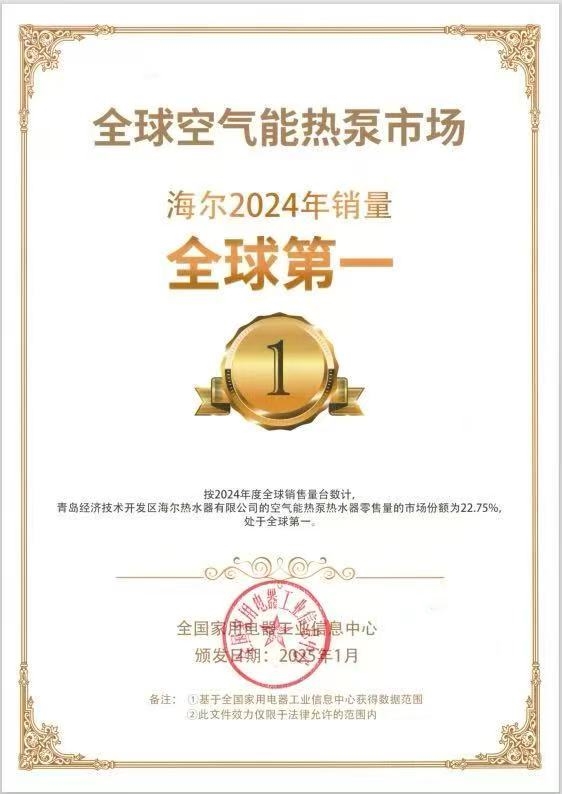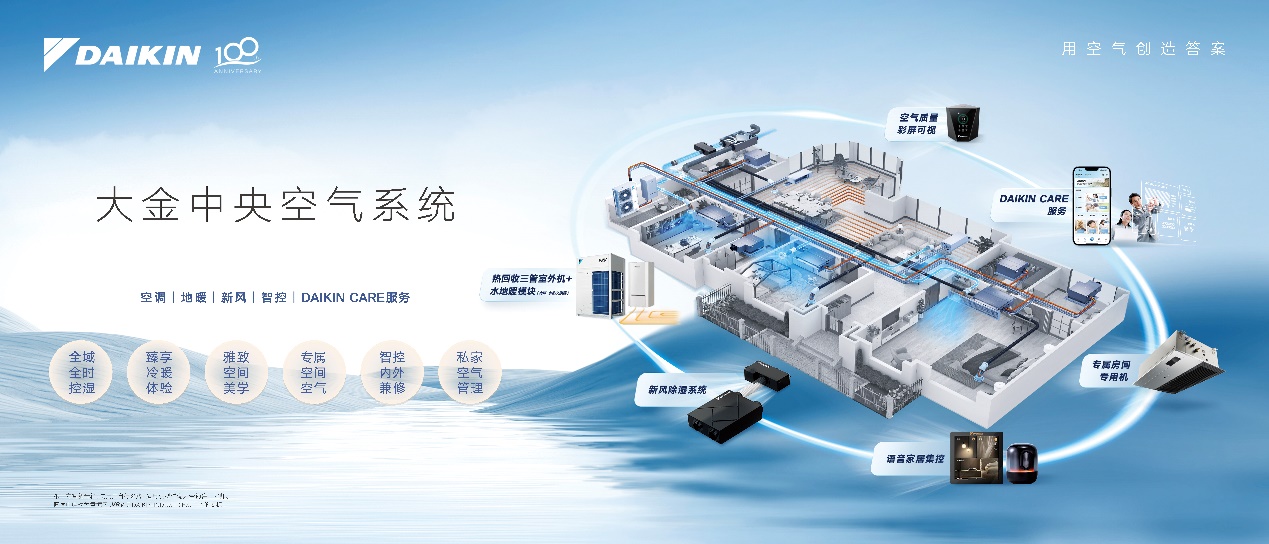“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校园不在名。”
——作者题记
我这里所提及的校园,它是鄂西恩施市郊的湖北民族大学。
30多年前,我在这里就读时,它被称为“鄂西大学”。
我和同学们当时佩戴的校徽,是一枚小手指大小的长方形金属牌,丝线粗细的红色长方形边框,其中是白底红色凸起的字样:鄂西大学。
这四个字因为是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亲笔题写的,所以体积不大而含金量很高。
学校的名字后来被改为湖北民族学院,再后来又被改为如今的湖北民族大学。
它从一百八十多年前的师范学校起家并变迁至今,估计各式各样的名字自然也不少。
鄂西大学,虽然它普普通通,但它是我生命中的又一个成长的摇篮。几十年过去了,它依然珍藏在我的心里。
恩施市郊土桥坝的三孔桥畔,沿河的岔路百米处往左拐,连接着一条顺着院墙的泥巴路而直达校门口。
记忆里的校园,诸多景物随着岁月的洗礼已经慢慢地淡化和渐渐地远逝了,但还有几处至今仍深深地印在脑海。
大门口顺院墙的那条土路的外侧,有一片荷塘,很应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的景致。
如果是在有月有风有蛙声的夜晚,也确实能找到那拨动心绪的触点。
那个时候的我,每当在夜灯下轻声地读着《荷塘月色》时,总觉得那些唯美的句子就是描写的那个地方,似乎还能看到朱自清先生披着衣服溜达在夜幕下的背影。
多年以后,我去清华大学寻找到真正的《荷塘月色》的发源地时,竟然惊奇地发现二者不仅有些形似而且又非常地神似。
院子里伫立着一些粗壮高耸的大树,已经记不起大概有多少棵了,也不记得它们究竟是杨树还是梧桐树了。
我想它们既然是守护者的身份的话,那么至今也许拥有百多年的树龄了。
这些树很普通也很朴实,很有《白杨礼赞》中茅盾所赞美的风骨,也好像是北京大学校园的那些名树,周围散发出相同的书香味儿。
印像深刻的还有那些一字型排列的许多栋教室和宿舍,全是仅一层的老式建筑,陈旧斑驳的白色墙壁,房顶全是盖的青色土瓦,学生睡的也是上下铺的木架子床。
操场旁边那幢老式教学楼颇有民国建筑的风格 ,大气而雅致,古朴而简洁,多少又有一点复旦大学古建筑线条的影子。当时,因为有了新修的教学楼,它就被降级为教室使用。轮换到在此处上课时,我心里总有一种怀旧之感。
记忆里的校园,不少的人物在无限思念的情绪渲染下,倒是越来越清晰明了。
首任女班主任姚萍女士,年轻美丽而又温文尔雅,和蔼亲切且又笑容可掬。次任班主任姓田,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我们给他取的绰号叫“板爷”,对我和同学们挺是豪爽大方的。还有给我们亲自上过课校长和众多师者的形象也都历历在目。
要说最难忘的应该是教写作课的恩师王正贵先生。
先生儒雅的身姿,清瘦的脸庞,略略下陷的眼眶,明亮的双眼放射出柔和而智慧的光亮。他说起话来缓慢且吐字清楚,我听他讲课时尽力不走神,总觉得每句话都比圣旨还重要。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诸如此类的经典章句,他是要求同学们必须要背得滚瓜烂熟的。
先生不仅有学问,而且还有故事。他二十多岁时,因为写了一篇名为《老车》的小说而被诬陷,他被遣送回他老家名叫三里坝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他每天在陡峭而曲折的山路背运木柴和牛草时,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做学问 ,常年坚持不间断,三十多年如一日。
先生五十多岁才得到平反而重返讲台,他用几十年的心血凝聚而成《作文构思300例》,它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获奖,自己也被评为“优秀教授”。
先生有次从上海出差回来,特意带了一套复旦大学的写作教材送给我并嘱咐要加强自学。他还教导我说“分数不重要,关键要有真本事。记住,从现在开始,你的作文不会给你打高分的!”
“守正而为贵。身正不怕影子歪,人生难免受到冤屈和误解 ,自己要静而应对才是!”这是毕业时他写给我的话。
先生传授的不仅仅是写作的技巧,同时也教导我如何做人的道理。
毕业后,先生经常给我寄来亲笔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我谆谆教诲的无限深情。我每次打开印有鄂西大学字样的信封时,就感到春风般的温暖扑面而来。多年后 ,我再也没有如期收到先生的来信了,因为他已因病辞世。
记得我们当时属于成人班,同学们来自各个不同战线的不同岗位,特别是年龄、身份.、阅历相差很大,很多同学的优秀品格和出众才华对我的影响和帮助都很大。一次,我把“白云深处有人家”里的“深”字写成了“生”字,年龄最长被称为“金老大”的同学当面严肃批评指正说:“你这个生字是无中生有的生哦!”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成为我学习和工作中要注重细节的警钟。
三十余载一瞬间,恩师同窗记心间;如今满头积霜雪,满盏感恩敬校园!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校园不在名。
附评论:
在平凡的土壤里生长出生命的诗意
——作家蜀水散文《校园散记——献给湖北民族大学》读后感
在高等教育日益精英化的今天,作家蜀水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将一所在历史长河中普通却深情的校园推至聚光灯下。作者以三十余年时光沉淀的笔触,在记忆的褶皱里打捞起那些被时代浪潮冲刷过的细节,用文字重构了一座精神的圣殿。这篇散文不仅是关于校园的回忆录,更是一曲献给平凡生命的赞美诗,在细微处绽放出人性的光芒。
草木砖瓦间的精神图腾
作者笔下的鄂西大学没有未名湖的盛名,亦无清华园的恢宏,却以三孔桥畔的泥巴路、斑驳的白墙、青色土瓦构筑起独特的精神图腾。那条顺着院墙的泥巴路既是通向知识殿堂的物理路径,更是生命蜕变的隐喻通道。当校园名称在时代更迭中数度变迁,那些守护者身份的参天古树却始终挺立,在年轮里镌刻着永恒的坚守。这种将物质空间升华为精神符号的书写策略,让普通校园获得了超越地理坐标的永恒价值。
在记忆的滤镜下,旧教室的上下铺木架子床与民国风格的教学楼形成时空的复调叙事。作者特意强调老教学楼被降级为教室使用的命运,这种今昔对比的张力,恰恰揭示了教育本质的永恒性——知识的传承不在于建筑的华美,而在于灵魂的碰撞。这种对物质表象的超越性思考,使普通校园成为了承载文明薪火的精神容器。
文章对校园细节的刻画堪称显微镜式的观察。小手指大小的长方形金属校徽,其丝线粗细的红色边框与白底红字的视觉记忆,在三十余年后依然纤毫毕现。这种对微小物象的精准捕捉,不仅体现着普鲁斯特式的记忆美学,更暗含着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生命哲学。当作者将校园荷塘与清华园的朱自清旧迹并置时,细节的相似性消解了名校与普通高校的等级差异,昭示着美与真理的普遍性。
朴素叙事中的生命史诗
在时空交错的叙事中,斑驳的白色墙壁与青瓦房顶构成了记忆的基底色。这些被岁月侵蚀的物质痕迹,在作者笔下反而获得了永恒的诗意。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笔法,源自作者对生活本质的深刻认知——真正的永恒不在于物质的坚固,而在于精神记忆的鲜活。当怀旧之感在新旧教学楼之间流动,细节的在场性已然升华为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作者对校园的情感不是喷薄的火山,而是深井里荡漾的月光。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珍藏二字泄露了三十余年未曾褪色的赤子之心。这种克制的抒情方式,恰如中国画中的留白艺术,在文字的间隙里涌动着情感的暗流。当记忆中的荷塘月色与清华园的实景重叠,时空的距离在情感的坐标系中消弭,展现出精神原乡的永恒魅力。
在这个崇尚名校光环的时代,《校园散记——献给湖北民族大学》以其诚恳的叙事姿态,重新定义了教育的本质价值。当作者在记忆的荷塘边打捞起那些发光的细节,我们忽然明白:真正塑造人格的从来不是大理石的校门,而是知识浸润心灵的温柔力量。这篇散文就像校园里那些普通而朴实的古树,在知识的土壤里生长出年轮般的诗意,提醒着我们:每个认真生活过的地方,都是值得用生命书写的圣殿。
平凡中绽放的师者光芒
在《校园散记——献给湖北民族大学》一文中,作者以素朴的笔调勾勒出鄂西大学这所普通大学里知识传灯者的立体肖像,镌刻下王正贵老师这道独特的人文景观。这篇散文不仅打破了名校方有良师的世俗偏见,更在师生互动的细密针脚里,编织出超越功利的教育真谛。
王正贵老师的存在本身即是对大学非大楼之谓的最佳诠释。当作者用儒雅的身姿凹陷眼眶中智慧的光亮构建起师者肖像时,一个在逆境中淬炼出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三里坝的崎岖山道、背柴山路上坚持治学的细节,反映出王老师大雪压青松而青松挺且直的生命状态。当《作文构思300例》这部心血之作在联合国获奖,那些浸透汗水的背柴岁月与困厄便获得了史诗般的回响。王老师用生命轨迹证明:真正的学术高度从不取决于讲台的华美,而在于思想者灵魂的深度。
意犹帅也的教学理念,守正而为贵的临别赠言,在王老师这里不仅是文学理论的传授,更成为塑造人格的密码。赠予复旦教材时那句加强自学的叮嘱,暗合《论语》中不愤不启的教育智慧。当学生“听他讲课时尽力不走神,总觉得每句话都比圣旨还重要”,展现的不仅是师道尊严,更是思想火种的传承。当老师刻意不给作文高分,实则是用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的严苛,锻造学生直面真实的勇气。这种超越功利的教育情怀,这种将写作之道与为人之道熔铸一体的教导方式,恰似禅宗师傅的当头棒喝,在看似冷酷中蕴藏最深的慈悲。
跨越时空的精神馈赠
作者对恩师的感激,并非止步于知识层面的感恩,而是升华为对精神父辈的情感皈依。这种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使师生情谊超越了世俗的施与受,升华为文明传承的精神仪式。当作者将老师的赠言化作生命的座右铭时,我们看到了教育最动人的模样——那是用灵魂点燃灵魂的永恒光焰,是在平凡中缔造不朽的精神馈赠。
文章中的感恩情怀具有双重向度:既有对母校培育的个体感恩,更暗含着对高等教育平民化进程的礼赞。作者特意追溯学校从师范学堂到大学的变迁史,在名称更迭的表象下,揭示出教育平权运动的深层脉动。这种将个人记忆嵌入时代洪流的叙事策略,使朴素的情感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
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同学情谊的珍视。作者笔下的同学们,尽管来自不同战线、岗位,年龄、身份、阅历各异,但他们的优秀品格和出众才华对作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金老大”当面严肃指正作者错别字的一幕,不仅体现了同学间真挚的情谊,更成为了作者注重细节的警钟,对其学习和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文章结尾处的“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校园不在名”,巧妙化用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意境,进一步强调了“校不在名有教则成”的观点,即学校的名声并非最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有教无类、育人为本的教育精神。此文不仅是对过往时光的怀念,更是对同学情谊和教育意义的深刻领悟。(蜀水 龙道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